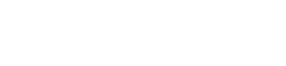志愿者手记 | 卢晟 · 三晋访书琐记
作为一位研习古籍保护学的研究生,如果要我概括在课堂所学,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版本目录与古籍保护工作的相关具体知识;其二就是见书目验、参与古籍保护实物实践的必要性。
鉴定版本的“观风望气”依赖于遍访群籍练就的慧眼,而熟练掌握工作的具体细节更离不开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在如此信念的引导下,我报名参加了本次“2024中华古籍保护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山西行”,参与这次普查编目工作。
山西省内各地皆不乏文物古迹。本次普查工作的目的地曲沃与高平,前者曾是晋国旧都,是著名的“曲村-天马遗址”所在地,亦是著名的“成语之乡”;后者则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故里和战国时秦赵长平之战的古战场,有着丰富的古建筑遗存。山西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我对接下来的访书之旅充满期待。

2024年7月15日,我们在曲沃县图书馆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普查编目的工作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确定书的名称与著者,二是核对册数与卷数、确定存缺卷情况,三是鉴定版本,四是测量版框与书品的尺寸,五是记录古籍的破损、老化、虫蛀鼠啮情况,六是记录藏版、钤印、批点等其他相关信息,七是书写馆藏题签,此外还要拍摄书影留作记录。
作为起步引导,来自山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的老师们以汲古阁本《春秋公羊注疏》为例向我们说明了编目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在曲沃县图书馆的馆藏中有相当数量的十三经,这些经部书籍版式行款基本一致的,但只有一部分是毛氏汲古阁的正品,其他的皆为清代的翻刻本——前者开本更大且刻印精细,而后者开本更小且字体与印制更加粗滥,此外还有版心下方镌字可作佐证,虽然二者非常相似,但细加对照下仍可鉴别区分。
这种正本与翻刻本的混淆只是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中的一种,对于不同的古籍,其记载版本与著者信息的方式各有不同,就需要在编目的过程中对内封、序跋、卷端、版心等各处进行翻阅。
古籍的损伤状况亦是千差万别,有的内封老化变脆,有的吸水膨胀变形、又经函套的勒压难以翻检,也有的蠹蚀严重、书叶稍不小心就可能破碎掉落......可以说,古籍普查工作中面对的最大的矛盾,就是如何在尽可能不损伤古籍的前提下、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翻检把握书中记录的各种信息。古籍的破损情况固然令人痛心,但是亲眼目睹古籍老化损坏的实际情形,也坚定了我做好自己工作的决心。
在曲沃县图书馆工作期间,我自告奋勇接下了一项重要任务——整理馆藏的《知不足斋丛书》。
《知不足斋丛书》是由清代藏书家鲍廷博所辑的一套大型丛书,其内容广博、校勘严谨、刻印精良,并附有鲍氏所撰写的多篇序跋,因而广受称赞。我依照《中国丛书综录》的著录对馆藏的《知不足斋》进行了清点,曲沃县馆藏的《知不足斋》为一至十集,每一集为两函十六册,其中一、二、九集各缺失了一函八册,仍存有十七函共五十五种。在将这些丛书彻底清点,单独编制表格进行记录并按顺序整理完毕后,我看着整齐摆放、尺寸小巧的十七函丛书,一种莫大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除了《知不足斋丛书》,我还得以见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古籍,其中既有贵族与文人编纂的家刻精本文集,亦有民间基层日常所用的医书、历书,更有清末的小说、戏剧唱本等等,其用纸、版式、刻印质量皆是天壤之别,但各有其不同的特色与价值。在这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二:
其一是曲沃县图书馆馆藏的清代嘉庆年续修的曲沃县志,其中以图文详细记录了古代曲沃地区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情况,对于研究曲沃县地理人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虫蛀破坏,该县志的天头已经破碎,书叶也几近脱落,这一县志也将在普查结束后被送往山西省图书馆进行修复。
其二是高平市图书馆馆藏的数册教材,从版心题字可知这套教材是民国时期由山西大学校出版的,这些教材采用英文撰写,近代石印方式印刷,依然保持了中国古籍的鱼尾板框与线装形制,虽然从出版时间角度已不属于古籍范畴,但这些融合古籍形制与西方新学的讲义仍不失为近代教育历史的独特见证。
本次古籍普查工作期间,我共为一百五十余种、合计六百余册古籍进行了编目,并拍摄了数十张书影。
在工作期间,我切身感受到,那些只能在图录与数据库中得以一见的书页成为了手中拥有空间体积的实体,而原本凝固于书本与讲授中的版本学知识在工作中得以活化、拓展。
在带队老师的悉心教导、身边同学的通力合作以及曲沃、高平两地图书馆的通力支持下,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攻坚克难,亦收获了诸多在课堂上难以取得的成果。
一位老师有言,古建筑的保护是与自然以及时间的对抗,而我觉得古籍保护亦是如此。虽说有选材精良、精制秘藏的善本可以做到“纸寿千年”而长久保存,但绝大多数古籍都要面对自然环境的侵蚀与千百年社会变迁而带来的离散。

我相信通过这从“2024中华古籍保护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山西行”,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将在当代古籍保护“对抗时光流逝”的宏大事业中留下一抹独特的亮色。
卢晟 天津师范大学